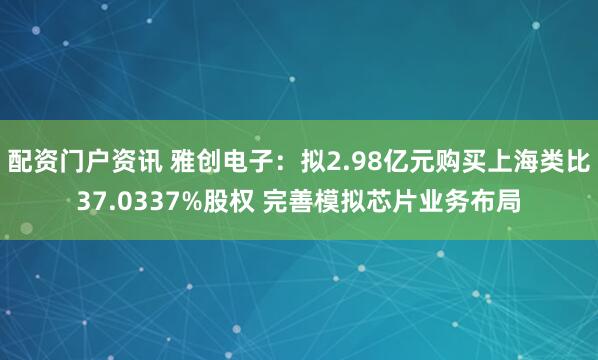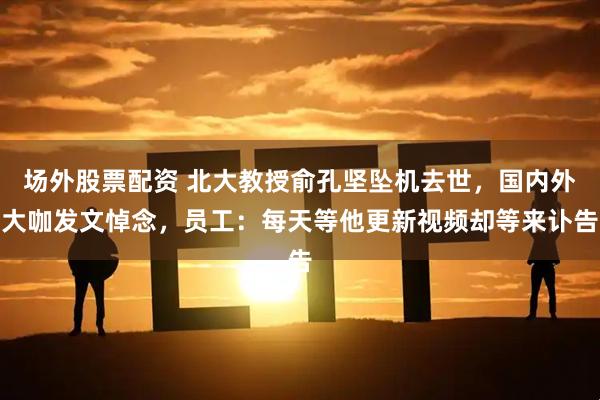冬日的阳光温暖而柔和,把人影拉得很长,走在熟悉的道路上,阳光洒在身上,温度渐渐升高场外股票配资,让我不禁有种想脱下厚重棉服的冲动,正如茅盾小说中描写的“直想把那棉服脱了去”。
与那些搬迁或已废弃的三线工厂相比,120厂依旧保存着相当规模。从一组航拍照片中可以看到,厂区沿公路两侧密集分布,但真正属于职工宿舍的区域,只有几个集中地。其它单独的小楼,基本是本地原住民所建。
从沟口步行到中区的灯光球场,这段路对我小时候来说显得漫长无比。这里曾是4131厂,信箱号113,官名大明仪器厂,而我所在的厂则是4170厂,保密代号为111信箱,广平机械厂。一个小溪把这片名为小孙家沟的地方自然分为东、西两个区域,两个厂被溪流分隔,坐落在南北两边,直到1983年两厂合并为广明无线电厂,也就是今天的120厂。
展开剩余85%厂区很大,分为南区和北区,南区以球场为中心,而北区则一直延伸到两公里外的黑石坡脚下。合并后的南区变成了中区,而以南大院为核心的区域则被称为南区。
沿着球场右边的小路上行,便是厂区的办公楼,这是我曾在这里工作多年之地。推开门,室内一片沉寂,开门的吱吱声在这静默的环境中显得格外刺耳,似乎在召唤那些曾经在这里工作的老员工。阳光透过门缝洒进屋内,尘土在光束中飞舞,仿佛在诉说着这里的荒凉与寂寞。
突然,我在家里翻出了几张老照片。1973年,那是4170厂第一次党代会的合影,照片中有我的父母;另一张是1979年,第三次团代会的合影,照片中我站在最后一排的左上角。看着这两张发黄的照片,记忆的闸门不由自主地打开,时光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流转,那些往事逐渐清晰,但又如梦似幻,难以触及。
时光继续流逝,我又回到过去的路上,走过70厂的大门,昔日的坐标镗床旁,那抹红色依然鲜明,把我拉回到那个激情四射的年代。似乎能听到工人们在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歌声中匆忙走向岗位的声音。
进入工厂,原先的值班室变成了小卖铺,那个“燕商店”的标志尤为显眼。对面,曾经的标语已经模糊不清,锅炉房依旧保留着当年的功能,给厂区供暖、供应开水和蒸饭。往后走,那座二层楼曾是机动科,如今成了一家颇具特色的咖啡屋,浓浓的怀旧氛围扑面而来。
走进咖啡屋,周围的一切都让我产生了穿越感。那老式的电话、厚重的工具书、过时的仪器、古老的台灯,都在努力拉我回到那个年代。继续沿路走,工厂的各个车间一字排开。一个车间的对面是二车间,曾是工厂的主力机械加工车间,承载着雷达基座的生产任务,现在却变成了羽毛球馆。空旷的厂房里,偶尔传来击球声,为沉寂的环境增添了一些活力。
我突然想起了C罗在世界杯上的一句话:“下山的路真吵,漫天的嘘声和当年欢呼声一样刺耳。”也许正是这些回忆,让我与那个机器轰鸣的年代产生了无尽的联系,仿佛每个角落都弥漫着切削金属的气味和忙碌的身影。
继续前行,我经过了六车间、注塑车间、五车间和装配车间。原本的礼堂,曾是工厂的电影院、剧场、食堂以及后来的十车间。这里曾是毛主席追悼会的场所,哀悼的哭声犹在耳畔;也是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,欢乐的笑声回荡在夜空下。
沿着礼堂旁的小路,我来到了三条岔路。最右边是我曾经的防区,厂供应科,从下料房到贵金属库,一路走到单身宿舍。左边是工具库,再往前便是医务室和曾经的721工大的校区。再走,便是北区,那里原本是家属区,现如今却荒凉一片。
一直向前走,我来到了四车间,后来变成了矿泉水生产厂,而汽油库所在的地方如今也荒废了,周围一片静默。山洞里的三车间,曾是瑞士进口齿轮加工设备的所在地,如今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。
我进厂的时间是1975年底,当时是分配到三车间,也就是那个山洞里。山洞里有最先进的齿轮加工设备,每天的风扇保持着恒温环境,工人们在这里舒适地工作。然而,随着90年代中期军品逐渐萎缩,收录机也难以与专业厂家竞争,工厂的困境愈发严重,最终走向了停薪留职、下岗的结局,除了少数员工,大部分人都被迫离开。
如今,那座山洞已经破旧不堪,透过门口的光线望去,犹如马里亚纳海沟般黑暗。听说它曾被租给农民种蘑菇,但那种微薄的收入早已无法挽回它的颓败。
四十年过去了,120厂就像一个被遗忘的孤岛,孤独地漂泊在城市的角落。周围的高速公路和园林设施让城市焕然一新,而120厂依然保持着冷清和无奈。站在曾经的球场边,回想着这里曾经的热闹和欢声笑语,心中却涌起一阵清愁。
世事无常,曾经的我们经历了文革、下乡、下岗等种种不堪的历史,而现在回头看看,已经是满头白发。岁月匆匆,我们走过的路比想象中更长更远。而如今,当我站在这个曾经的起点,看着夕阳染红了天际,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心悸,仿佛一切都已走到尽头。
发布于:天津市金多多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